我们已经看到,科学家们花了数十年时间,已经对电磁辐射了解得非常透彻;而且通过许多研究,证明了日常生活中的电磁辐射并不会对人体有害。
但是,为什么这样的谣言依然流传这么广泛,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呢?
这要从我们自己的大脑说起。
我们大脑的“套路”
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大脑,让我们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了数百万年,但是却并不适合现代生活——今天的世界已经变得太复杂,那些让我们在大草原上如鱼得水的本能,已经不够用了。
即使是今天,我们在看到一则信息时,第一反应都是信以为真。怀疑和查证更花时间、更费脑筋,只能是之后的自我反思。我们脑中的“套路”,力量十分强大。
可能有害,就会记住
我们会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,恐惧、愤怒和悲伤对大脑来说更有力量。“人类总是更看重消极信息”,北爱荷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海伦•哈顿说道,“这具有进化上的意义。知道如何躲避一头老虎比知道哪儿的花开得漂亮更重要。”
在这些负面情绪中,恐惧容易滋生谣言。一个群体的焦虑感越严重,就越容易变成谣言工厂。正如罗切斯特理工学院谣言专家尼古拉斯•迪方佐所说,我们通过传播信息化解恐惧和未知。即便交流的信息是荒诞的,交流本身也能给人一种知晓事态的感觉,来平抚不安。“谣言的一大功能就是试图挖掘事实,让人知道该做什么。”我们想要知道些什么,哪怕不是事实也没有关系。
所以,当我们看到一则让自己担心的信息——比方说“变电站会让人生病”时,大脑就会更重视,也就会更容易记住它。至于这是不是真的,大脑并不在乎。
“包治百病”更好记
看看你攒了多少稀奇古怪的“常识”吧:吞下的口香糖排出体外要花七年。大脑利用率只有10%。太空中能看见中国长城。一个人每年在睡觉时平均吃八个蜘蛛。电脑桌上摆一盆仙人掌可以防电磁辐射。
这些小知识简单有特点,描述生动,便于记忆。但它们都是错误的。不过这正说明具体、易于理解的流言更容易深入人心。“复杂的观点不好传播,” 邓肯•瓦茨说,“观点在传播时会丧失详细内容。”谣言就像传话游戏,传了几次细节就没了,变得更加简单。
古斯塔夫-勒庞在《乌合之众》里就大众心理有过非常精辟的论断。如何让一件事情变成信仰,三步走:断言、重复、传染。谣言也是类似。大脑喜欢简单和确定,不喜欢复杂和模糊,所以更容易接受绝对的事物。
越奇特,越好记
浏览一下那些被无数次转发的故事,“一个人在酒吧喝醉,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装满冰的浴缸里,旁边有一张纸,上面写着‘打电话叫救护车,否则你会死。’结果发现后腰两侧的伤口,原来双肾被偷走了。”“一个50多岁的教授,将他太太生完小孩之后的初乳放入了一个玻璃瓶里,然后用蜡封口放入一个盒子,打算等到小孩长大结婚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小孩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小孩要结婚了,教授把封印了二十多年的盒子打开,是一瓶红色的液体。对,是血。”
这些谣言初听起来有点诡异,但是似乎还有点道理。不符合常规的东西更容易让大脑记住,而且人们总会想让别人也知道这些神奇事物。它们与已有知识一致——犯罪分子很可怕,器官移植很紧俏,喝醉了以后会毫无知觉令人摆布;母亲哺乳很伟大,女人会分泌乳汁和经血。只要内容不是太过火,很多人的常识就不会警醒。
简而言之,我们的大脑本来就偏爱谣言。
我们容易被影响
人类是社会性动物。我们生活在人群之中,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,而这些影响,正是谣言传播的最好温床。
从众效应
基本上打着“据说已获得1000万转发”“50年研究证明的惊人结果”作为标题的文章基本都是谣言。这属于营销手段,纯属骗转发骗关注,和推销畅销书美容品的手段是一样的。
人们都有从众心理,这也算是大脑的本能之一——当我们混迹在同类中时,就不容易被捕食者吃掉。我们虽然在衣着打扮上尽可能和他人不同,但是在脑中,我们依然渴望与其他人抱有同样的信念。
利用这种心理,谣言就变成了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大家都知道,所以是常识;所以是正确的。在这种时候我们不会去想,也许大家都错了呢?
迷信权威
已知某饮料中含有咖啡因和苯甲酸钠;国家A类精神药品中有一个叫苯甲钠咖啡因,于是有人得出结论说该饮料可以治疗精神病。你会相信吗?
没有专业背景,我们只有依靠其他线索辅助判断。如果结论出自一边喝饮料,一边看药盒的孩子之口,你肯定不会当真;但如果出自专家,你很可能不会怀疑。我们相信那些更知名、更有权力的人,却很少想一想,这些资历是否能让他们在某件特定的事情上做出正确判断。
果粒橙中检查出多灵菌,本来让人恐慌,但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说“没事”,由于FDA一贯严谨可靠,大家就算吃下一颗定心丸。相信权威是迅速判断真假的捷径,但有时也会被无良者利用。药品广告上让演员穿着白大褂正是利用了“权威效应”。
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专业知识,无法判断对错,只能在信息源中选择看起来靠谱的。因此,动员足够人手或媒体,集体表达对某信息源的信任,他们就会在跟着信。说起来,对电磁辐射的恐慌,正是在有意误导下,迷信假权威的后果。
厌恶损失
“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”是我们对厌恶损失的最好描述。我们甚至会因为对担心可能的损失而放弃现有的收益。近几年出现过几次小区居民投票表决拆除手机基站的新闻——为了避免极低剂量的电磁辐射,人们居然愿意让自己忍受无法打电话的不便。
对损失的焦虑还推动着我们把信息传播出去,以帮助更多人避免蒙受损失,心理学家约拿•伯杰在统计了《纽约时报》的分享数据后发现,那些能够激起人们焦虑情绪的文章,更容易被分享给他人。
于是,谣言就这样一波波传开了。
直觉已经不够用
我们的直觉,是帮助我们快速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,是内置在我们大脑里的反应,快速方便。
但是直觉并不适合用来解决复杂问题。今天日常生活中涉及到的科学和工程,都已经变成了需要经过长时间学习才能掌握的专门技能,再用直觉来解释,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。
相关不一定有因果
前两年,曾有一项有关“看电视时间和死亡率”的研究大受关注。研究者在六年里跟踪了8800人,观察他们的健康、生活习惯和看电视行为。研究结论表明,每天看电视超过4小时的人,死亡的风险几率要比每天看两个小时以下的人高出46%。
这份研究被很多人概括为“看电视时间太长容易死亡”。这是个典型的把“有关联”解释成“因为所以”关系的例子。在这项研究中,研究者研究的并不是看电视,而是久坐和健康的关系。看电视只不过是常见的久坐行为而已。研究结论是,久坐与心脏病等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增加,而不是看电视会让人更容易死亡。
或者想想这件事:太阳升起来时公鸡会打鸣,但我们不能说因为公鸡打鸣,所以太阳才升起来。
吓人的概率
《新科学家》文章问道:如果有人告诉你,100个人里面,有25个人会因为癌症而死亡,又有人告诉你,1000个人里,有250个人会因癌症死亡,这两者哪个让你更担心?
清楚的读者一看就明了,这两组数字表示的是同一个比例:四分之一。但是,我们的直觉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,会认为后者似乎更严重一些。乍一看,数字越大,风险看上去也越大。
有几项研究对这个问题做了实验,给出了两组说法:“癌症导致1万人中1286人死亡”,“癌症导致100人中24.14个人死亡”,事实上,后一组说法的癌症风险几乎是前一组的两倍,但是,读到前一组说法的人却比后一组读者认为癌症风险更大。《判断和决策》也有同样研究,面对两组实质一样的说法———“每天有100人死于某种癌症”,以及“每年有36500人死于这种癌症”,读者会认为前者的癌症风险更小。
直觉不会算比例,只会靠第一印象。
相对风险并不“绝对”
我们可能看过这样的研究结果:每天吃一个培根三明治,会让患肠癌的几率增加20%。这个数据是用来衡量健康风险的。也就是说,如果你每天吃一个培根三明治,和不吃培根三明治的人相比,得肠癌的比例会高出两成。听起来很吓人,是吗?
但这些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,真正增加了多少风险。
普通人在一生中得肠癌的可能性只有5%左右,所以就算你每天都吃培根三明治,一生中得肠癌的比例也只是5%加上5%的两成——加起来也就是6%而已。这样听起来就没那么可怕了,是吧。
用相对风险而不是绝对风险来形容某种危险或者某种疗法的效果,这是最常见的误导方式。根据德国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心理学家吉根瑞森的《认识风险》所说,这类技巧称为“误导定义”。这,也同样是直觉处理不了的事情。
谣言流传广,辟谣困难多
谣言不可怕,如果辟谣及时的话。但是因为上述种种问题,谣言总是跑得飞快,而辟谣的影响力却小得多。
谣言的优势,刚好就是辟谣的劣势。对于科学研究来说,很少会有非常确定的结果,往往是在许多限制条件下谨慎地表示“很可能无害”;而且它提供的是关于“有益”的正面情绪,和那些靠恐惧和焦虑为养料、击中人们厌恶损失心态的谣言刚好相反,也就天然地缺乏传播能力,也不容易被很快记住。
谣言总是先于辟谣出现。人们在受到谣言的刺激后,对获取同类信息的需求就会下降,而且第一印象往往很难改变。只要过一段时间,谣言就会生根发芽,变成人们笃信的事实。所以“造谣动动嘴,辟谣跑断腿”也并不只是一句牢骚。
所以对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,等待辟谣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。更好的办法是自己去识别谣言,自己做出正确判断。如何避免受到谣言影响呢?请看下一篇文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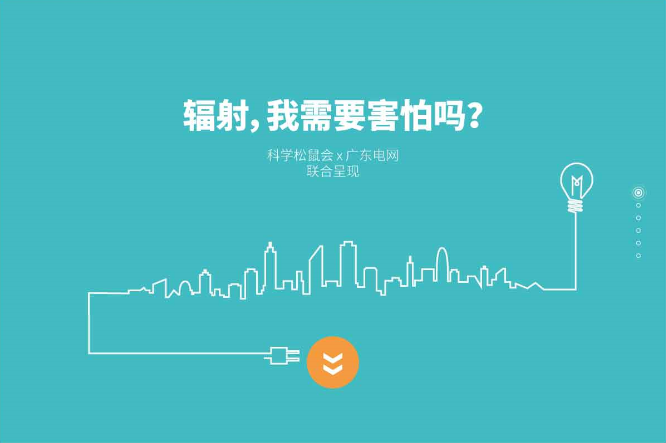
你的评论